第一本诗集
我年轻的时候,在北京读书,就常常写诗,我并没有准备出版,只是留一个纪念。有时候,是我老师顾随先生评点的。我保留了这些诗,一直没有出版。
到了台湾以后,发生了白色恐怖,我先生被关了,我也被关了。经过这一次的变故以后,就整理旧的东西,找到这一批旧稿子。我先生说,你这么乱丢,等一下遗失了,不是很可惜?他说我帮你抄下来吧。他就跟我教书的学校借来一个钢板,他就用钢板写了,就印了这么一本。被我的一个学生看见了,学生说这太不好看了,而且我先生书法也不是很好,所以那个学生就说,我用铅字打一本吧,他就拿去用铅字打了一本,都没有出版。
一直到一九六几年了,那个时候呢,我在辅仁大学、台湾大学、淡江大学教书,然后1966、1967两年到美国教书,1967年暑假我回到台湾,又回到台大、辅仁和淡江教书,那一年,在辅仁大学跟南老师碰见的,他当时也在辅仁大学教书。辅仁大学在台北市郊区,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区,所以辅仁大学就派一个车去接我们来上课。恰好我跟南老师上课是同一天,也是同一个时间,所以辅仁大学的车子就一路把我们接去了。我们都是中文系的老师,在一个休息室,南老师对于诗词很有兴趣,我们在一起就聊诗词。南老师偶然从学生那里看到一本我的打字的诗词稿,他说你出版了吗?唉呀,我说这是小的时候随便乱写的习作,不值得出版。南老师他说,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嘛,你不出版太可惜了嘛。所以他就拿了一本学生打字的稿子,他很热心地说,我要交出版社给你出版。
我跟南老师从开始认识到谈话、同事只有一年时间,我就又出国了。出国后,1969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,这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,是南老师帮我出版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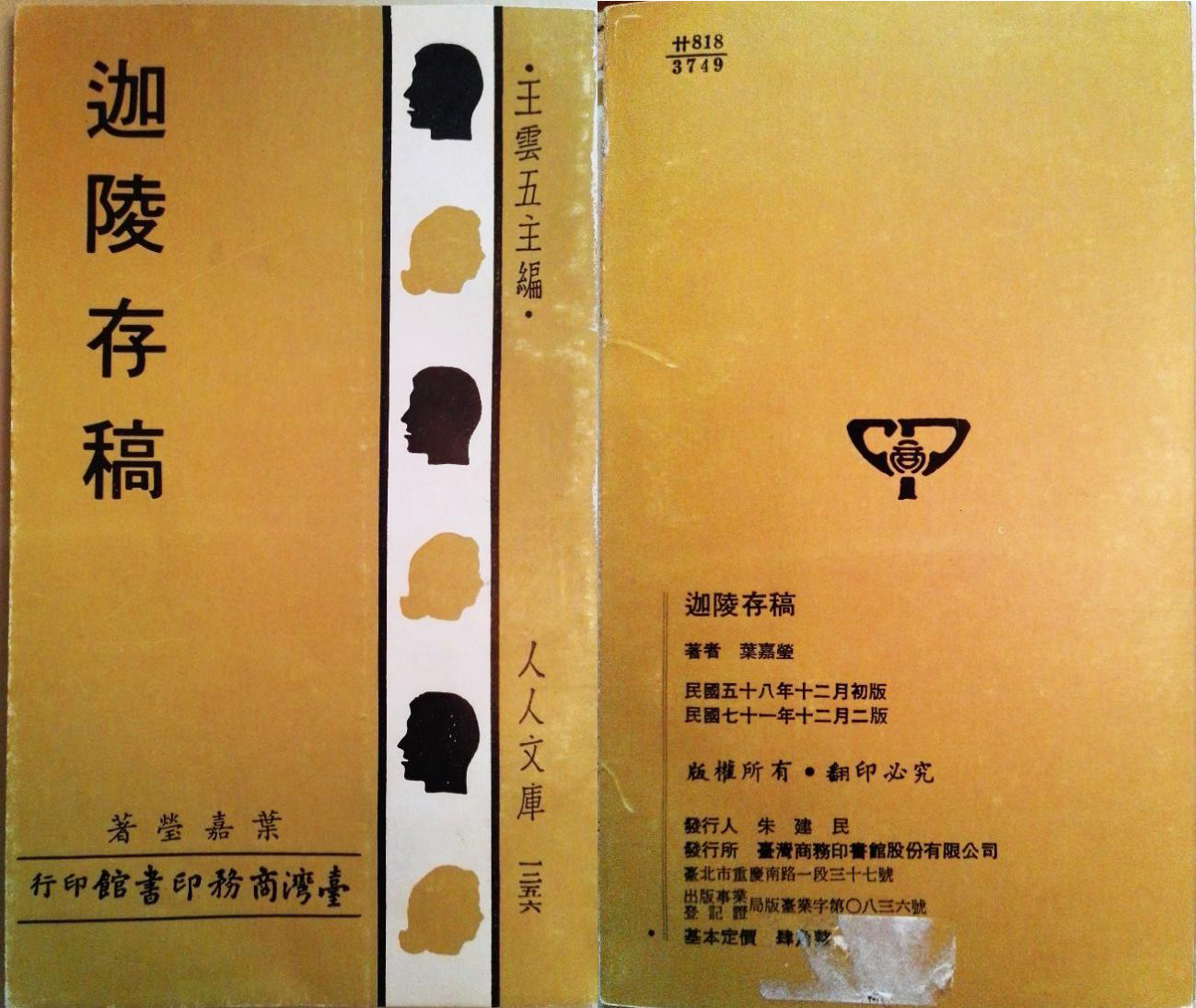
一段挫折
一年的相识,南老师不但帮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,还帮了另一个忙。
我第二次出国,本来是要回到美国去教书,因为我本来在美国已经教书两年了,我有一个exchange的VISA,就是交换学人的签证,是很容易随便来往的,是不限制的。可是因为这次我要接我父亲出去,美国说你有移民的嫌疑,所以在台湾没有办成功签证,不但没有办成功,他就把我原来的那个签证cancel,就是取消了。
当时,因为哈佛大学聘我教书嘛,哈佛大学说试一试到温哥华来签,我就换了一本新护照。
去加拿大之前,南老师就说,我有一个朋友,你可以去看看他。然后那个朋友就给我算一算,整个的批语我也没有带出来,我只记得两句,他说“时地未明时,佳人水边哭。”
那么,我就拿我的新护照到温哥华来办美国的签证。签证的时候,因为我是要到哈佛去教书嘛,所以我要拿哈佛的聘书,这样呢,你将来就可以教书嘛,不然你只是旅游的签证。领事馆一看,他说你已经拿到美国的聘书,你现在从台湾来,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办这个签证呢?为什么你换了新证跑到我这里来签?他说我不能给你签证,他说你要签,我要把你的这个新护照还送回台湾去签。但是台湾不给我签,我才换了新护照过来嘛!我就说那我不去了,我就拿回来了,拿回来护照就不能去美国了。
那我就打一个电话告诉哈佛大学,我说你们叫我经过温哥华过来,我已经到了温哥华,可是温哥华还是没有给我签证,所以我只好还回去了。哈佛大学一个教授,一直跟我合作翻译,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成英文,我帮他把一些中国的诗词翻成英文。这位教授非常希望我留在北美,他说你不要忙着跑回到台湾去,你先等两天,我替你联系一下。然后他就联系了我后来教书的这个UBC,就是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(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),他就给UBC大学的系主任打了电话,说有某某这样一个人,现在温哥华,本来是要到美国,没有拿到签证,你们那里有没有机会,给他一个临时的教书机会,可以留下来。
天下事很巧,那个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,他的中文名字叫蒲立本,他听到以后就说,唉呀,那太好了,我们正在找这样一个老师。他说本来我们UBC在亚洲系没有博士生,今年新设立了博士班,有两个从美国UCBerkeley(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)过来的学生,巧的是呢,这两个研究生都是研究中国唐诗的,一个是研究韩愈,一个是研究孟浩然,他说我们正发愁找不到他们的导师,他说太好了!所以我就临时留下来到了UBC大学。
当时我是经过一段挫折,发愁不知道到哪里去,还是回台湾吧。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。这就是我要去加拿大之前,南老师介绍我去见一个朋友嘛,这是我到温哥华写的第一首诗:
异国霜红又满枝,
飘零今更甚年时。
初心已负原难白,
独木危倾强自支。
忍吏为家甘受辱,
寄人非故剩堪悲。
行前一卜言真验,
留向天涯哭水湄。
(原注:来加拿大之前,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,卜辞有“时地未明时,佳人水边哭”之言,初未之信,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,故末二句云云。)
注里提到的友人,就是南老师介绍的那个朋友,他告诉我就是我不会很顺利地到美国,就这么一段挫折。我就觉得这个朋友的话真是太灵了,跟我的遭遇完全吻合嘛!
再度见面
那么在1968-1969年之间春节的时候,南老师就跟我说,他说我在今年的春节会有一个禅修班,他叫我去参加。可是他定的日期是正月初一到初五。那我说,过年时呢,我是家庭主妇,我有父亲有先生还有两个女儿一起过年的,我这个主妇没办法跑出去坐禅啊,我说我没有办法参加,没有那个自由了。
如此呢就过了很多年。我到了加拿大的UBC大学,大学马上就决定给了我终身聘书,那我就决定留在了加拿大。我就一直留在那里,就没有跟南老师再见面。这样又过了很多年。到了80年代末,南老师到香港了。他到了香港以后,就有朋友告诉我说,南老师现在到香港了。那么恰好有一年,我被香港中文大学请去客座地讲课。我就打听到南老师的联系办法,我说从前他很热心的帮我出书,还介绍朋友为我占卜,那我现在到了香港,一听说南老师也在,就打了个电话。南老师就说,那你今天晚上过来,我们一起吃饭,所以我就去了。
南老师好像经常都是高朋满座的,去了那,他家里很多很多人,各个领域的,可是那一次他并没有机会跟我仔细地谈话。因为那一次,咱们国内很有名的演过康熙大帝的焦晃先生去拜访南老师,他是诚心诚意地要跟南老师学习坐禅的,所以虽然南老师叫我去了,我们都见了面,可是南老师那次主要的是答复焦晃先生的问题,还有很多人要跟他谈,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谈。南老师可能一直希望我也跟他学禅,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,没有跟他学习过。
讲学万佛城
不过我自己与佛家另有因缘,那也是很有趣的事。
我在加拿大UBC大学教书时,有个学生的师父是宣化上人,她就跟我介绍宣化上人。有一天宣化上人到温哥华金佛寺来,我的学生陪他过来,那我就跟她到了金佛寺。宣化上人坐下来以后,大家都等着他讲,他就跟我说,今天我不讲,今天请你上来讲。我说我不懂佛法,我讲什么呢?他说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临时就想到陶渊明的诗:
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
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
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我就讲了这首诗,就说啊,这个寺庙虽然是在闹市之中,但是很清静,没有喧闹的生活。我讲完后,宣化上人说,你讲得非常好!还叫他一个大弟子,是一个美国白人,但是中文好得不得了,他说你把叶老师讲的用英文讲一遍。他这位大弟子真的是讲得非常好,把要点都抓住了,很优秀。然后宣化上人说,以后每一个礼拜,你都到我们这金佛寺来讲一次。于是每个礼拜六,我都到金佛寺去给他们讲讲陶渊明的《饮酒诗》,饮酒诗有二十首,我没有讲完,因为我每年暑假都到中国来讲课,所以我就说对不起大家,我要去中国了,课就停下来了。
三年以后,我又回到温哥华。我那个学生已经出家了,又来找我说,师父说你上次二十首还没有讲完,还差了三首,这次我们请你到万佛城去讲。我也很好奇,也没去过万佛城,我说好,我就跟她到了万佛城。讲完了,他们就叫我还接着讲杜甫什么的。我有四首绝句,就是在那期间写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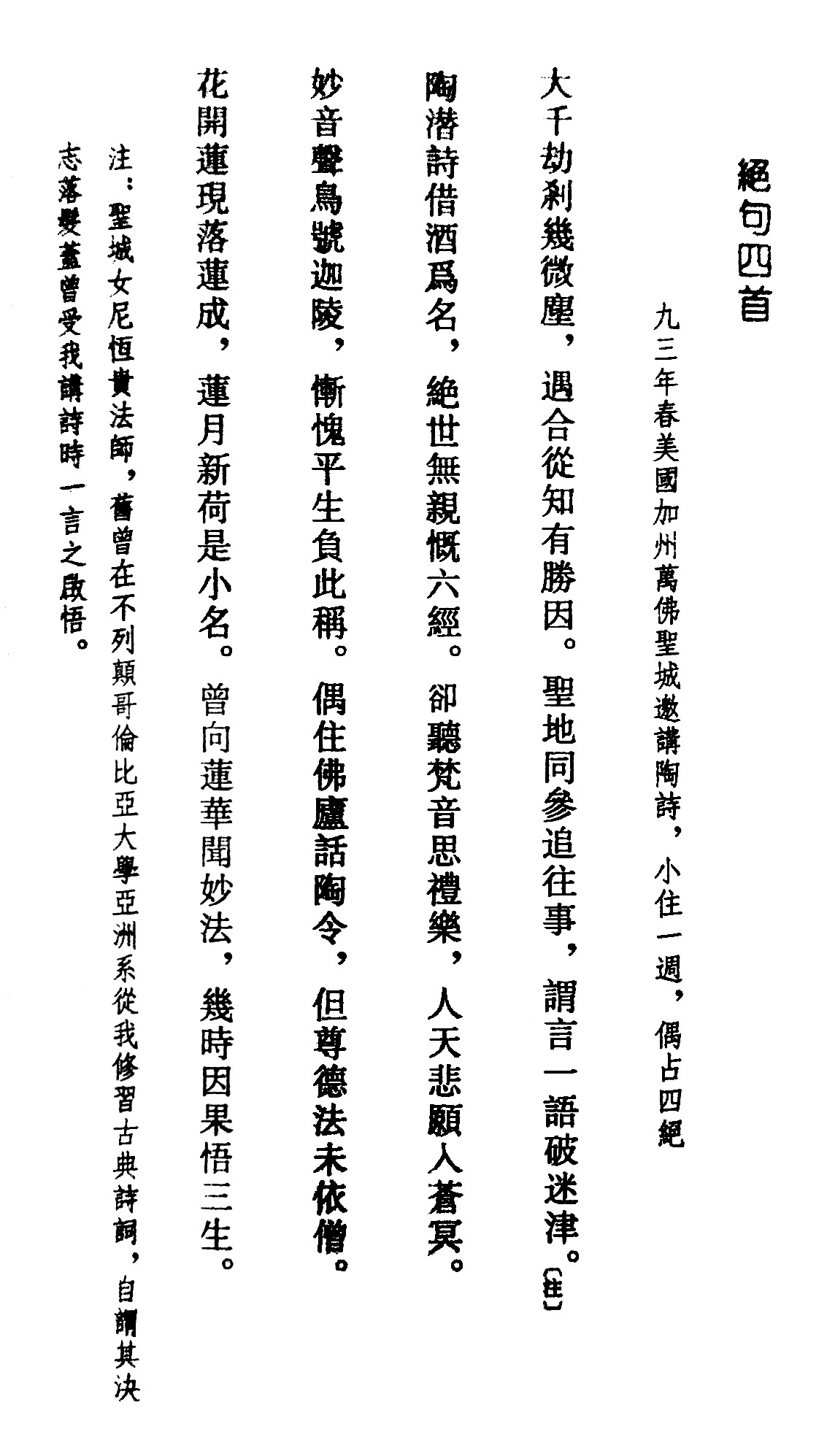
第一首,“大千劫刹几微尘,遇合从知有胜因。圣地同参追往事,谓言一语破迷津”。“谓言一语破迷津”,我问我的学生,我说你怎么决定出家了?她说是因为我的一句话,什么话呢?有一次她要选做报告的题目,我说你要做报告呢,应该选一个有价值的题目,不要做那种无聊的题目。我说这人生的选择,你要选择一个重要的。她说就因为我这句话,她做了人生的选择,出家了。
第二首,“陶潜诗借酒为名,绝世无亲慨六经”,陶渊明在饮酒诗里边,曾经慨叹说,现在都没有人读六经了。“却听梵音思礼乐,人天悲愿入苍冥”,我们在万佛城的客人,有一个客人的住所,在万佛城的靠西边的地方。大殿在靠东边的地方,每天早晨天还没亮,我就听见大殿钟磬齐鸣的诵经声音,我觉得非常的美好,我就写了这首诗。

第三首,“妙音声鸟号迦陵”。因为我的笔名就是迦陵。我十几岁在家里边读诗词,我的伯父喜欢跟我讲一些个故事。我的伯父说,清朝有一个词人陈维崧,很有名,他的作品很多,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,迦陵就是佛经上的妙音鸟的名字,全名是迦陵频伽。他说在陈维崧以后,好几十年以后,有清朝另外一个词人叫郭麐,郭麐号频伽,因为他仰慕迦陵,所以他叫频伽。这是我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。那我在大学里边呢,我喜欢作诗填词,就交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。顾随先生就说,你的诗词写得很好,我要给你拿出去发表,他说你发表过什么作品?我说没有,我从来没有想发表,他说我拿去发表,你想一个笔名吧,我想了想说,就叫“迦陵”吧。所以顾先生就把我的诗词发表了。我这个人也很简单,也不愿意再起别的名字,所以从此我就叫了迦陵。“惭愧平生负此称”,就是对妙音鸟惭愧,平生负此称。“偶住佛庐话陶令,但尊德法未依僧”,我在他们那讲陶渊明的诗,宣化上人他们对我很尊重,我也尊重佛法,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佛家的仪式。
第四首,“花开莲现落莲成,莲月新荷是小名。”这怎么讲呢?我小时候,我们家里是不信任何宗教的,没有跟任何宗教的人有往来,我家里只相信孔子。可是我到了大学以后,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有时候喜欢讲一些禅宗佛法之类的,他喜欢讲,那我就想,我也应该知道一点吧。有一天,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,说北京广济寺请了一位佛教的大师讲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我就想,因为我是六月出生,我小名叫荷,就是莲花嘛,我就想,这个我要去听一听。所以我就跑去听讲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所以说“曾向莲花闻妙法,几时因果悟三生。”是讲这一段因缘。那我对佛法本来也不大知道,我只记得他讲的主要意思。说“花开莲现落莲成”,就是人人都有佛性,你还没有成佛,那你的种子在那里花开就有这个莲现了,是要你把世界的尘俗挂碍都解脱了,你这个莲才结成。我听讲以后就记得这么几句,当时说法的法师的话。
诗词学会与赵朴老
跟这个广济寺后来还有因缘,这又过了好几十年了。1988年,中国成立了一个诗词学会。因为我到处讲诗词,在那一年的春天被我们辅仁校友会,联合四个单位,邀请我在国家教委的大礼堂讲中国诗词,一千几百人的一个会场。我本来不肯讲,我说唉呀,我这只教教书,在班上讲一讲,你弄到北京来这么大的场面,而且不是说讲一次,是一个系列,我说万一讲砸了,怎么交代?我们校友会说反正已经请了很多人,一定要我讲。我只好讲了,结果听众反映很好。
然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诗词学会。当时来开会的有赵朴初先生。那是个大会,我是主讲人,我就在台上讲。讲完了,诗词学会的人就介绍我跟参会的这些有名的人士见面,然后我就回家了。过了两天,就有一个人送来一封赵朴初先生的信,信里说约我到广济寺去吃素斋。巧的是,到广济寺吃斋的那一天,是我阴历的生日,是六月初。去了以后,我就告诉他,我说你约我来这里太巧了,这是我几十年前第一次听讲佛经的地方,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有一首词记述这件事:
“当年此刹,妙法初聆,有梦尘仍记。风铃微动,细听取、花落菩提真谛。相招一简,唤辽鹤归来前地。回首处,红衣凋尽,点检青房余几。
因思叶叶生时,有多少田田,绰约临水。犹存翠盖,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。西风几度,已换了微尘人世。忽闻道,九品莲开,顿觉痴魂惊起。
(注:是日座中有一杨姓青年,极具善根,临别为我诵其所作五律一首有“待到功成日,花开九品莲”之句,故末语及之。)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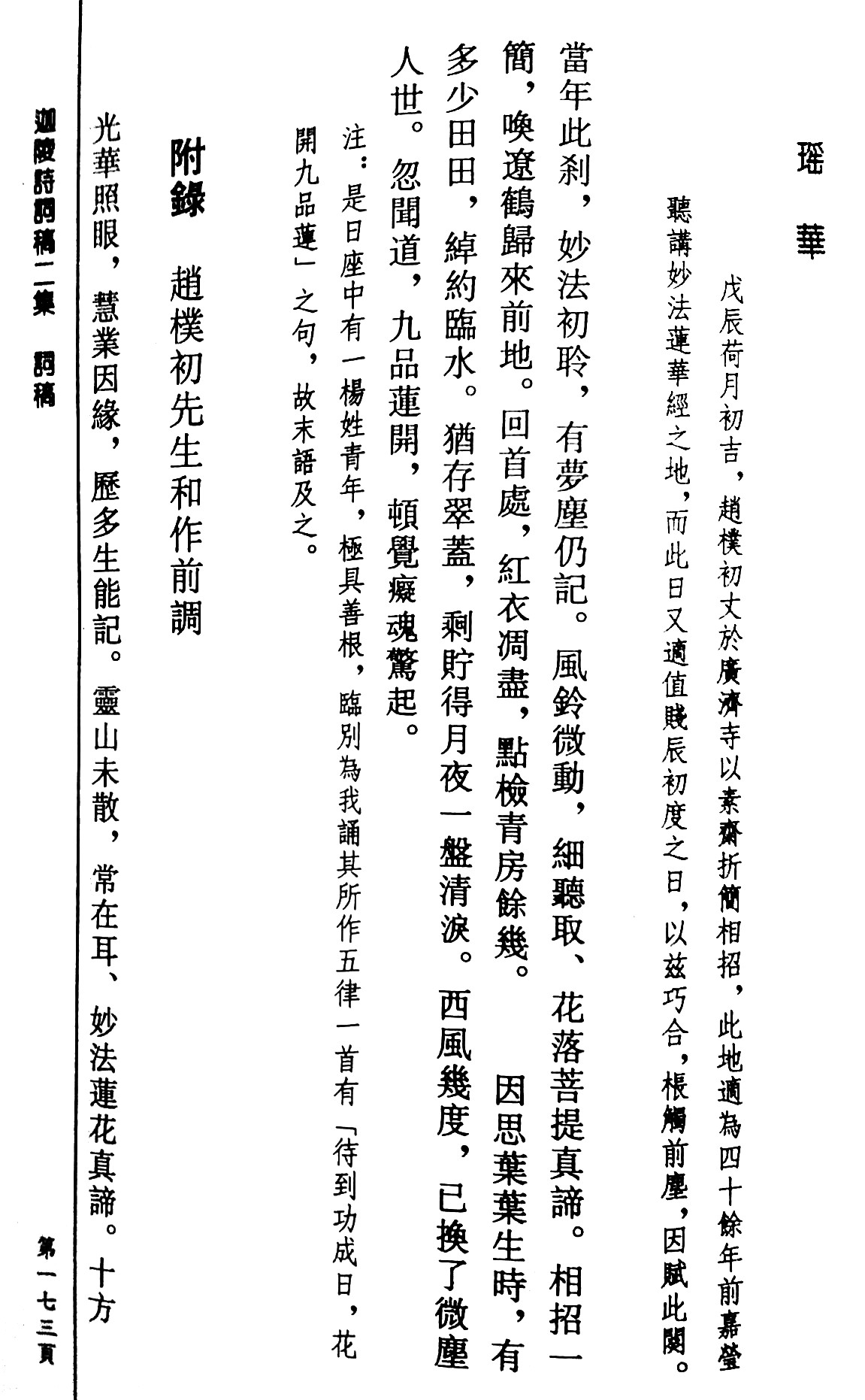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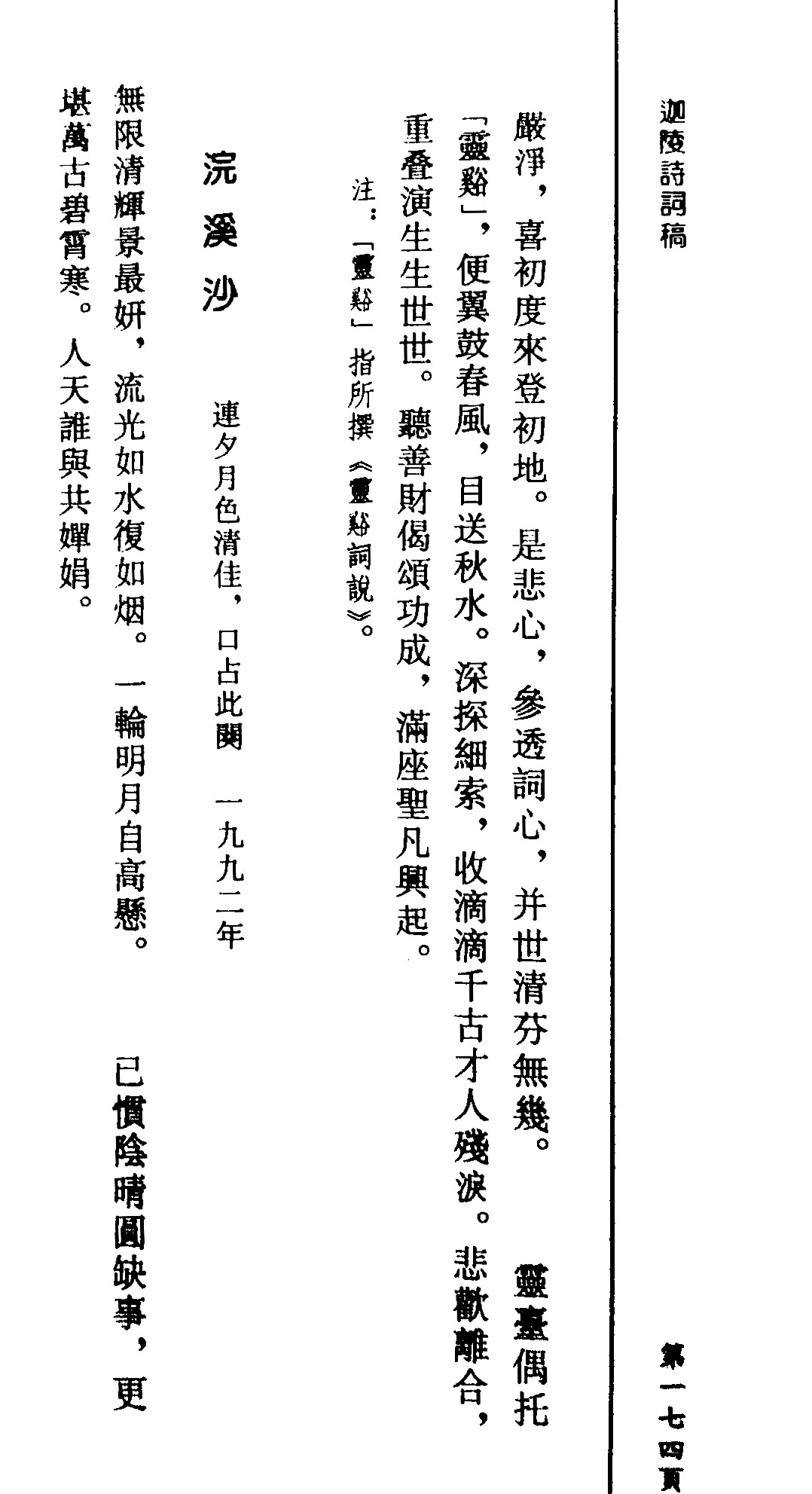
后来赵朴初先生还和了我一首词:
“赵朴初先生和作前调:
光华照眼,慧业因缘,历多生能记。灵山未散,常在耳、妙法莲花真谛。十方严净,喜初度来登初地。是悲心,参透慈心,并世清芬无几。
灵台偶托‘灵谿’,便翼鼓春风,目送秋水。深探细索,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。悲欢离合,重叠演生生世世。听善财偈颂功成,满座圣凡兴起。
(注:灵谿指所撰《灵谿词说》。)”
赵朴初先生对我非常好,第一次他送请柬约我去吃饭,是请一个人送来的。他这首词写好了以后,毛笔写了,亲自送到我察院胡同老家。我们老家本来是个大四合院,解放以后变成一个食堂什么的,后来变成居委会,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。那我回家以后呢,我就临时住了非常小的一个房间,一张桌一把椅一个床,没有别的地方再可以放东西。赵朴初他看到我住的地方这么狭窄,朴老就说,我们佛教会在北京还有一处房产是空的,他说你可以去住。我说这个不可以,因为我也不是回来常住,我是放假才回来,我那时候在UBC,我还要回到加拿大,我说我不能够要一所房子,所以我就谢绝了。我们家里人也都很好,都不要,这个身外的意外的东西。其实我两个弟弟住得也很紧。朴老后来常常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,我出版的书他都看了。
顾随先生的勉励
我可以说是不用功的人,因为我并没有好好去研读佛经,我也没有去拜哪一位法师,都是我自己的探索,没有什么形式。我这个人从来不大注意这些外表的,比如写诗词就写了,并没想说要怎么样怎么样,现在也是,反正我讲了就讲了,可是大家把它记下来,这样子的。
我的老师顾随先生,对我是有很大的期望,他有一封信给我说,我听他很多年的课,凡他的所有法我都得到了,他说我所望于足下者,是于他的法外,别有开发能有建树,成为南岳下之马祖,不要做孔门的曾参。然后他还讲了一句,然而欲达到此目的,非取径于蟹形文字不可。他的意思就是说,我光读中文还不够,我真的要想开拓,一定要学好英文。可是那个时候你想,我们在国内而且是在日本控制的沦陷区,没有英文课,没有这个机缘。
可是天下事情就是如此,我不是后来临时去了加拿大的UBC大学嘛,他们有两个研究生,所以需要一个导师。可是后来他们系主任跟我说,作为一个专任的教师,你不能只教两个研究生,你一定要开大班的课,大班的课你一定要用英文教,这对我是一个挑战。我这人其实是很用功,我在中学在大学都是班上的第一名,我是很会念书很爱念书的人。所以他让我用英文教书,那我就真的用功,我就每天晚上查生字,而且我的学生连我的博士生们所有的论文报告都是英文啊,所以我就要查生字备课,用英文讲,所以给我逼了几年,那我的英文就进步了。我这个人还真是很好学,我说英文好了,能够对付我的课,这个我还不满足,一是我真好奇,同时也是喜欢学习。而且我在国外教书的那几年,可以说那是西方的学术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,有名的学者过来讲演,我就去听,现在那个时代都过去了。
后来我从加拿大退休了,又回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去教书,还是教我的诗词。清华大学晚上有一个课,一个教授讲西方很出色的一个女学者关于西方的解析符号学,我就去听。从她那里学来之后,我用到我的诗词上来。我后来写了很多篇论文,用西方的理论来讲了中国的诗词,就讲这个诗歌的语言,它不是逻辑性的,它是感受质感的思维,这个语言就是如此的。所以王国维说词有什么好处?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。谁也摸不清楚,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所以我学了他们西方这一套,就写了很多论文,用西方的理论把中国词的特别微妙的地方说出来了。可是这个方面,我中国的学生,他们不能够继承和发挥,因为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英文太差,我真的用西方理论写的东西,他们并不大能够继承。那在外国,他们是用英文的,又没有中文的修养。
可是我又要说了,不是说我的聪明才智胜过了王国维,或者胜过我的老师。是王国维的那个时代,西方还没有这些个理论。王国维也很用功,他后来也学英文。我的老师本来就是英文系的。可是他们那个时代,西方还没有这些理论出来。
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事情,对人对事我都是尽我的力量去贡献出来,其他就随缘了,这也是佛法的一个道理。
我认为我教书或者研究诗词,还是属于知识学问。可是佛法是证悟,不是知识,超越一般的知识。
南老师大概一直要度化我跟他参禅。在这一方面我没有经验,没有机缘,就是跟南老师没有这一份机缘,因为他叫我去参禅,我没有去成嘛,所以没有机缘。但是我虽然是没有能够跟南老师有这一份机缘,但是我后来另有与佛家的机缘。我在台湾那会儿,在辅仁大学,那个时候还有一位叶曼老师,好像当年也在辅仁兼过课,她跟南老师学禅的。后来我在北京见过她,那时候她90多岁了。
南老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而且知识方面也非常的渊博。南老师那会儿跟我谈话,大致都是讲诗词,他对于文学很有兴趣,对于我的诗很感兴趣介绍去出版,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在辅大上课时都见一次面。
(本文根据录音整理,2018年10月21日定稿)
- 还没有人评论,欢迎说说您的想法!
